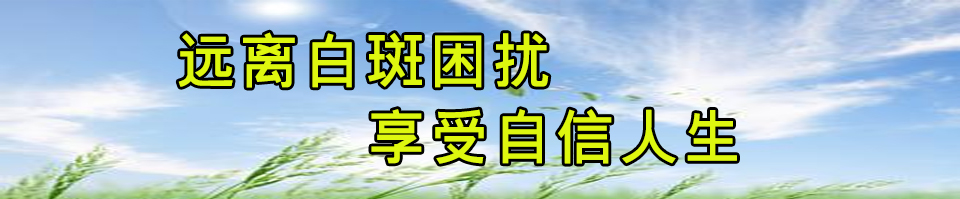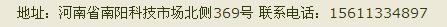谁是热带水果里最能做菜的
不同野生杧果种类的果实(上)和芒果的不同品种(下)。1,2来自马来西亚,分别是马来巨果杧(M.pajang)和一种果肉是白色的杧果(M.caesia),两个都酸,这其中一个或者两个的果皮会腐蚀皮肤,因为两个是一天捡的,不知道哪个是祸首。3是来自版纳的林生杧果(M.sylvatica),纤维很多,吃起来像蘸了汽油的甘蔗去掉甜味。芒果虽然品种很多,但常见的就只有几大类,这里列举的当然不全,4小台芒,5鹰嘴芒,6肯特芒,7不认识但很大的芒。小台芒很甜,鹰嘴芒很汽油,剩下两个都是肉多核小一个顶一顿饭那种
芒果树上芒果配色的杧果白条天牛Batoceraroylii(Hope,),理论上会蛀食杧果的树干,”芒“和”杧“其实可以通用,但提到植物的时候我更喜欢用杧,而芒果用来特指杧果的果实
提到杧果就忍不住说一下假杧果科(Irvingiaceae),假杧果科下只有十几个种,大多数种类在非洲热带。亚洲分布最广的就只有马来假杧果(Irvingiamalayana)一种。假杧果科和漆树科并没有太大亲缘关系,但马来假杧果的果实很像野生的杧果,不仅颜色黄绿,种子也是侧扁且和果肉结合紧密。当地人会吃假杧果的果仁,据说是杏仁的味道。
泰国清迈看到的马来假杧果,离中国也不算远,不过国内没有分布
假杧果科冷门到有时候会被误看成五加科的常春藤(Ivy),《中国天牛彩色图鉴》中记载的常春藤尼克天牛Nyctimeniustristis(Fabricius,)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个译名来自资料记载的寄主植物,但原文中并不是“Ivy”而是“Irvingia”,假杧果科的学名是为了纪念19世纪苏格兰的外科医生兼植物猎人EdwardGeorgeIrving而和常春藤(Ivy)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个天牛实际上应该是”假杧果尼克天牛“。
勐仑的”假杧果尼克天牛“,它飞起来时触角上的两段白真的好飘逸。尼克天牛属最近被修订并在版纳描述过一个新种,照着文章里的检索表揣摩了半天也没看出来这只的腿是算是红还是不红,暂定是这个种,哪个大佬如果比较熟悉求指正
回到正题,杧果之外、国内分布最广也最广为人知的漆树科野果恐怕算是南酸枣属的南酸枣(Choerospondiasaxillaris),这个名字应该是为了方便北方人和结出小红果的灌木状酸枣划清界限。对于南方人来说,”南“字大可省去,酸枣从来就是这种秋天掉下鹌鹑蛋大小、黄绿色果子的大树。南酸枣一般的吃法是做成点心酸枣糕。酸枣糕虽然早就吃过,味道和北方的酸枣真的很像,也是为什么直到去年看华农兄弟的视频才把南酸枣和酸枣糕联系起来。南酸枣种子的主要传播者是咀嚼能力很强的麂属,所以种子也要硬核,挡得住一副好牙口,我们当然没有辜负南酸枣的这个特性,把种子串起来做手串,还起了个美好的名字叫做五眼菩提。五个圆形的斑纹对应着雌蕊的五个心皮,在左边的果子上还能看到残留的柱头痕迹(那两个褐色的小点)
野酸枣,滴溜溜地圆,北方人印象中的酸枣(Ziziphusjujubavar.spinosa)是鼠李科枣的一个变种。
槟榔青属的分布就没有那么广了,听说过的人也更少。槟榔青属的原产亚洲热带和美洲热带,但果实的去腥能力一流,成了各种热带料理中绝佳的调味品。原产南太平洋小岛上的甜槟榔青(Spondiasdulcis)的栽培和利用遍布世界热带,国内也有引种。甜槟榔青,图自维基百科,CC
中国原产的种类槟榔青(S.pinnata)的分布在云南南部、海南和广西。槟榔青在版纳被叫做“嘎哩啰”,这个名字的来历我并没有查到,只知道这多半不是来自傣语,因为槟榔青在和傣语一脉相承的泰语中被称为Makok,(”Mak“在傣语里也是果子的意思,甜槟榔青是Makokfarang,直译为外国槟榔青)。槟榔青也有很长的果柄,成熟时黄绿色,但果核的硬度有限,应该也是果蝠传播种子。槟榔青,比甜槟榔青的果子更小,核更大,不过味道类似
槟榔青的树叶和树皮
曼谷路边摊的海鲜沙拉里的槟榔青,那些条状的是青芒果,忽略里边让人提心吊胆的贝类和那个有点发臭的鱼头的话简直好吃到要死
中国原产的另外一种槟榔青属植物岭南酸枣(S.lakonensis)的分布更偏东(连酸枣和南酸枣都分不清的人哭了),岭南酸枣的成熟果实更小、更圆、红色,很显然吸引的对象是能看懂颜色的鸟类和灵长类,但除了当野果生吃,反倒没有听说像其它槟榔青属植物那样料理上的用途。广东乌禽嶂自然保护区的岭南酸枣,图自西子江生态保育中心李成,作者授权,转载请注明:http://www.lonkn.com/wazz/119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