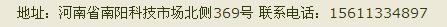南山之南
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郑华国 http://news.39.net/bjzkhbzy/170628/5496667.html文&图/时兆娟?小学校在环县公路的旁边。来来去去的班车从这里走过的时候,会因为一招手而缓缓地停下来,班次不多也不少:半个小时一趟,等车的间隙刚好够东南西北地观望一圈。再回头的时候,便能看到灰围巾般的来路上,摇摇晃晃的车子前边用红字醒目地写着“方城—古庄店—小史店”。你坐上,车子上不多的几个人,车门便缓缓阖上了。我就住在这个长方形小院的西头。朝向南。好天的时候,秋阳不烈,搬一张凳子坐在旗杆台旁晒太阳。三棵大雪松又粗又高。有一枝向东北角斜逸,末梢恰好钻过楼上的栏杆。雪松的枝条很坚韧。幸亏楼上住的孩子们不像我小时候那般淘气。要不,伸手拽着枝条荡秋千是个很不错的玩法,或者,抱着树身从上面“哧溜”滑下也不错。要是时间长了,会把雪松的树皮磨得像白桦一样光滑吧,我想。不过,现在的孩子都“傻”,他们被家长训得不敢冒险,不知道那种刺激能带给人多大的快乐。晒太阳的时候院门锁着。孩子们正好下课,在院里来来去去地追打嬉闹。透过门棂,能看到远处的小山,马头一样伸到河坝里的渡槽。山不高不巍峨,有着鲫鱼背一样裸露着的石脊。不远,隔着一块收割完花生空荡荡的土地而已。其实学校背后也是山。还很有名,叫子房山。对,就是那个汉初“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张良。山上最有名的,一是有不规则形状的花岗岩巨石,石底有类与人面像的线刻。据说巨石还被人为撬动过。使人不得不怀疑在某一个具有神秘气息的夜晚,一个或一群外星人披着红色的披风,外套红色的裤头来到房山,变出一把金刚钻,在巨石上以自己为原型刻出一个线条凌乱的人物图,又恶作剧地将巨石翻了个个,然后“嘿嘿”坏笑着飞走了。山上还有一种摞摞石,体型之庞大,形态之怪异,只能有这样一个解释:某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张良心中郁闷或者忧伤,甚至快乐也说不定,神仙的心思你别猜,因为猜啊猜啊凡人也猜不出来。总之张良就拿出一只笛子或者箫,呜呜咽咽的声音清越悠远,吹得月亮羞答答蒙起了面纱,吹得星星眨着眼睛吃了醋,吹得不远处黄石山上的张三丰恼上心头。这张三丰人称“张爷”,是道教的祖师爷,也是个有个性的人。他曾经在值班做饭包饺子的时候关上门,后来被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凡人趴门缝里偷窥,见他居然往锅里屙饺子。你说这是多恶心人的一件事。那两个凡人自是坚决不吃,结果不知底细吃了的人连同鸡啊狗啊的都慢悠悠升天了,就剩这俩人在地上急得直蹦了。回头说这张爷,可能又是照三不着凉的错过了饭点在那加餐,反正他做事一向特立独行难以捉摸,吃的五谷或者清风都有可能。这时正刮南风,张良的笛声忽然传来,张爷大怒,用手里的筷子夹了一块石头扔了过来。张良正在入神,忽然觉得脑瓜子后面一凉,准准确确判断出这是他人生中遇到的无数支暗箭中的一支。他也不回头,只是从从容容地伸出右手,抓住了那块带着啸音的黄石,伸手摞在了近旁。后来,子房山上的摞摞石被载入了史册,上边还有只有专家能参透的“岩画天书”。很多的专家学者来考察,平民百姓去烧香,闲着没事的大姑娘留守小媳妇去拍抖音。于是山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年代久了,淤泥把当初张良清修的”张良洞“都淤塞得找不到洞口了,只剩下一丛青竹掩映在洞口。我老是不想和那络绎不绝的人们碰面。于是就日日想着南山,想着那马头一样伸到河坝里的渡槽。
上一篇文章: 卫计委发布药食同源原料目录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秋末冬初的一个晴天,我终于抄过那块收割完了的花生地,直奔那山涧水流汇成的河坝而去。
落在地里的花生陆陆续续发了芽,有的还是两片肥厚的子叶,有的长出了十处八片圆圆的青叶子,松软软的,舒展展的。但不管这时再怎么蓬勃,将来也长不成气候去,寒霜一降就会枯萎,谁让他们生不逢时。这就是人生的道理。道理这东西,没有不好,多了也不好。随随便便看见一种事物就发感慨,方言里说叫“神经病”,就是读书多了脑子被烧坏了的意思。所以参透之后,我一般不叹息“勘透人情惊破胆,参破世事凉透心”,我只是像个月白风清的哲人一样把词人的“天凉好个秋”引入生活,而且要翻译成方普,就是方城的普通话:“咦,今儿个的天真好真凉快啊”。其实我连这也没有参透,你说谁能参透呢?他说曾经“壮岁旌旗拥万夫”,而今“春风不染白髭须”,耿耿于怀于万言平戎册换成了邻家种树书。其实邻家老头压根就不想要,那东西烧锅又不起火焰,哪如种菜能吃能卖多实惠。他又絮絮叨叨教育儿子按数缴纳公粮,然后“管竹管山管水”,和那些个普普通通的老公公和娘家爹没有什么区别。让人觉得他写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的清新也不过是日升日落里偶然的一次浪漫文艺范,和我此刻的黄土地上一袭大红长衫没有区别,加上秋风吹动长发,可以想像自己身在天宫,娇若仙女。沿着七十年代修的台阶下去,走到了两尺宽的河坝上。七十年代的水泥颜色发灰,就显出用白石子摆出的“反帝反修”的字样特别醒目。用手摸摸余温还在,那余温来自当初修建时,一个村里十二个村庄的壮劳力闲月时候聚在这里,吃过饭就匆匆忙忙上工,去南山崩石头,用架子车“嗨呀嗨呀”拉回来的热度。然后勾点很不容易买回来的水泥一块一块往上垒,一直垒了三四层楼那么高的基座,再改用“秦砖汉瓦”的蓝砖券。用了整个冬春,硬是铺出几里地平展展的空中水渠来,向南延伸到到南山之南,两旁的庄稼都有了保证。河坝的一侧建有水房,而今房顶坍塌,房里裸露,当初那种崭新的大型水泵一发动,清凉凉的水花翻卷着进入渡槽的辉煌早已不在。一个老头拿着铁锹,将锹臂长度能够着地方的淤泥一锹一锹挖出来,说是趁闲月挖出个能存放水泵的水坑,以备天旱时放置自己的水泵抗旱。他看我从坝上走过时,对坝外裸露的石质河底和坝内绿水里漂浮的植物感兴趣,连忙给我解释说,这不是城里人宝贝一样买回的入侵物种水葫芦,而是一种野生的菱角,还没有结。我这才注意到确实是被形状差不多的叶子给骗了。菱角大体是一棵一棵分散长在水里的,绿油油的叶子,营养很足,一副衣食无忧的小理想满足的得意。不远处,一个钓鱼的人钓住了一条小鱼,手忙脚乱地将鱼绳拽了上来,将那条不幸的鱼儿取下放入泡在水里的鱼篓里,鱼篓红色的上沿在绿水里一浮一漾,里边已经有了几条瘦长的鱼儿,隔一会儿不甘心地想往上窜窜,又无可奈何地落回牢笼。渡槽就筑基在整块的岩石上面,南山乃至南山之南的南山都是一整块的岩石,石质坚瓷,色呈灰白。一窝一凹的地方,积存了上古留下来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土,也就长出了一小片一小片的红薯和芝麻。构树不成林,高高矮矮,枝枝叉叉地盘绕地头。一棵桑树挺拔高大。不久后,经霜一打,蝴蝶样落下的枯叶就是一种上好的药材—霜桑叶。而在这个过去了的夏季,它的树枝上一定挂满了或紫或红的桑葚,只是不知道有没有孩子像我们当初那样爬上高高的枝头,将捋下后洗也不洗的桑葚往嘴里捂。那时候,野地里有那么多带有甜味、苦味、酸味、辣味的东西,可以填进我们永远也不会饱撑的小肚皮,有那么多的乐趣藏在这无边无际的大自然里,和我们躲着迷藏。我有一次爬上高高的白杨树,去捉一只头上长着黑色“辫子”、硬壳会飞的“吱吱牛”,眼看胜利在望,忍不住得意忘形地往更细的树枝上走了一步,只听“咔嚓”一响,我的小身子便离了弦。地母盖亚并不仁慈,她赏我半个月的休学躺着不动。后来,我就抛弃了爬树的绝活,在地上捉蚂蚱逮蚂蚁,烧熟的蚂蚱和活着的蚂蚁肚味道有多不同我最有发言权;而找马包和酸酸豆也是不同的感觉体验。只是蚂蚁今天去了哪里?渡槽的下面,隔一段就有几棵酸枣树。红艳艳的酸枣就在荆棘中勾引着涎水。酸枣皮薄肉薄核儿大,甜味也淡。烧瓜只有一片一片生长的空棵。夏天的时候,它会结出肚子大两头小像小擀杖一样的烧瓜,甜甜的。狗娃花花瓣薄薄的,黄色的花芯在淡紫色的花瓣包围之中,细瘦的茎秆轻轻摆动;鬼针草又叫灰灰圪针,走路的时候不小心就挂满了裤腿,上边的倒钩刺使得它很难被摘下来。我姥姥说灰灰圪针熬水治血压降血糖益寿延年,所以她一碗碗喝得参汤似的满足。我坐在南山上微微喘息。南山之南,还是南山。
西边的山洼里传来拖拉机的响声,像是个咳嗽的老人,忽高忽低,忽粗忽细:“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它冒着黑烟吧,劳累把它变老了。连村庄上升起的炊烟都不想和它沟通。炊烟只扭动着细长的腰肢,在目空一切中上升,上升,散开成淡淡的雾岚……南山上,我遇到了我的童年。多少年了,我一点一点遗失了我的梦境。连我自己都觉得那些梦境的虚幻和不真实。今天,我却在这里和他们重逢。酸崩崩和天天豆,酸枣和烧瓜儿,瓦松和爬爬草,白翅尖的喜鹊和灰吐噜的麻雀,还有,还有,还有明年春天会爬出来结得坷垃上一闪一闪都是网的蜘蛛,红色内翅一碰就尿尿的花大姐……南山之南还有什么,我要一步一步走过去。等我在滚滚红尘中戏谑生风,笑骂如常,谁愿和我共一个少年的梦境:骑着竹马,穿过鱼戏莲叶,走进青蓝色稀薄的雾岚笼罩之下的南山之南?*作者︱时兆娟:南阳市作协会员、二月河文化研究会会员、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方城七小教师、7,转载请注明:http://www.lonkn.com/wazz/11939.html